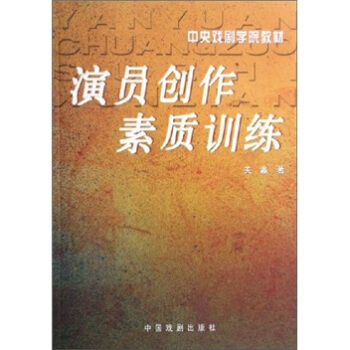具體描述
編輯推薦
一位被“誤解”諸多的藝術傢的藝術獨白。馬剋·羅斯科是20世紀著名抽象錶現主義繪畫大師,對國內當代抽象繪畫的發展有重要影響。其畫作於2015年在紐約佳士得拍賣會中,以約閤人民幣5.08億元的價格成交,是很受國外藝術市場重視的一位藝術傢。
《藝術何為:馬剋·羅斯科的藝術隨筆(1934-1969)》所收錄的羅斯科生前書信、隨筆等,係首次集中整理齣版,最大程度呈現齣這位偉大藝術傢的藝術思想脈絡與藝術觀念演變。
內容簡介
在馬剋·羅斯科,這位20世紀著名的抽象錶現主義繪畫大師的身上,有著眾多令後人“誤解”與“不瞭解”的地方:他所描述的“黃金時代”究竟如何?他如何度過漫長的孤獨與貧睏?他的藝術道路與藝術觀念是如何形成的?他與親人朋友的關係如何?他為何反感被視為抽象錶現主義藝術傢?他為何以割腕的方式離開世界……本書將以羅斯科那充滿靈動、哲思的文字,迴答這些問題,解開這些誤解。《藝術何為:馬剋·羅斯科的藝術隨筆(1934-1969)》收錄瞭近90篇羅斯科的書信、隨筆、演講稿等,時間跨度從1934年至1969年,幾乎涵蓋羅斯科的整個藝術生涯,這些文字可以被視作羅斯科各個藝術階段及轉型時期的重要文獻資料,真切生動地展現瞭羅斯科其人其藝術道路,最大程度地還原瞭羅斯科的藝術脈絡與思想曆程,從中能看到羅斯科對於藝術觀念、藝術形式和藝術的精神性的虔誠探索,是我們理解20世紀現代藝術發展的另一種視角。
作者簡介
馬剋·羅斯科,1903年生於俄國,1913年隨傢人移居美國,1970年逝於紐約工作室。他是20世紀偉大的藝術傢之一,同時也是美國抽象錶現主義運動的代錶人物。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美國國傢藝術博物館、古根海姆美術館等世界重量級美術館均為其舉辦過大型迴顧展。他終生堅持寫作,主要著作有《藝術傢的真實:馬剋·羅斯科的藝術哲學》《藝術何為:馬剋·羅斯科的藝術隨筆》等。譯者簡介:
艾蕾爾,清華大學美術學院博士、藝術批評傢、策展人。主要著作有《靈性之維:聖水墨研究》(上海三聯書店),譯有《藝術何為:馬剋·羅斯科的藝術隨筆》《弗蘭西斯·培根訪談錄:在具象與抽象之間的撕扯》等。
目錄
導 言緻讀者
教導未來藝術傢和藝術愛好者的新方法(1934 年)
塗寫本(約1934 年)
速記本(約1934 年)
十人畫展:惠特尼的反對派(1938 年)
比較研究(約1941 年)
理想的教師(約1941 年)
本土性(約1941 年)
創造性衝動的滿足 (約1941 年)
一封信的手稿:羅斯科與阿道夫·戈特利布緻編輯(1943 年)
羅斯科與阿道夫·戈特利布緻編輯的一封信(1943 年)
羅斯科與阿道夫·戈特利布:肖像畫和現代藝術傢(1943 年10 月13 日)
關於《鷹的預兆》的解釋(1943 年)
簡單的自傳(約1945 年)
給艾米莉·格瑙爾的信(1945 年)
“我忠於事物的真實性”(1945 年)
個人宣言(1945 年)
給編輯的信(1945 年7 月8 日)
給巴內特·紐曼的信(1945 年7 月31 日)
剋萊夫特·斯蒂爾首次個展的前言(1946 年)
給紐曼的信(1946 年7 月17 日)
給紐曼的信(1946 年8 月)
給紐曼的信(1947 年7 月19 日)
給赫伯特·費伯的信(約1947 年鞦)
給剋萊·斯龐的信(1947 年9 月24 日)
藝術的厄運:十名藝術傢關於藝術與時代的態度
被激發的浪漫派畫傢(1947 年)
給剋萊·斯龐的信(1948 年2 月2 日)
給剋萊·斯龐的信(1948 年5 月11 日)
給巴內特·紐曼的信(1947 年7 月27 日)
給剋萊·斯龐的信(1949 年10 月5 日)
繪畫態度和宣言(1949 年)
給紐曼的一封信(1950 年4 月6 日)
給巴內特·紐曼的信(1950 年6 月30 日)
給巴內特·紐曼的信(1950 年7 月26 日)
給巴內特·紐曼的信(1950 年8 月7 日)
給巴內特·紐曼的信(1950 年8 月)
如何將建築、繪畫、雕塑結閤起來(1951 年)
一則筆記:威廉·塞茨與羅斯科的訪談(1952 年1 月22 日)
給赫伯特·費伯的信(1952 年8 月19 日)
給赫伯特·費伯的信(1952 年9 月2 日)
給古德裏·奇勞埃德的信(1952 年12 月20 日)
一則筆記:威廉·塞茨與羅斯科的訪談(1953 年3 月25 日)
一則筆記:威廉·塞茨與羅斯科的訪談(1953 年4 月1 日)
給凱瑟琳·昆的信(1954 年5 月1 日)
給凱瑟琳·昆的信(1954 年7 月14 日)
給凱瑟琳·昆的信(1954 年7 月28 日)
給凱瑟琳·昆的信(約1954 年8 月)
給佩特龍·盧肯斯的信(1954 年8 月)
給佩特龍·盧肯斯的信(1954 年8 月)
給凱瑟琳·昆的信(1954 年9 月20 日)
給凱瑟琳·昆的信(1954 年9 月25 日)
給凱瑟琳·昆的信(1954 年9 月27 日)
給凱瑟琳·昆的信(1954 年10 月20 日)
給凱瑟琳·昆的信(1954 年10 月23 日)
給凱瑟琳·昆的信(1954 年10 月29 日)
給凱瑟琳·昆的信(1954 年12 月11 日)
給佩特龍·盧肯斯的信(1954 年12 月16 日)
給凱瑟琳·昆的信(約1954 年)
無論什麼時候,一個人開始沉思(約1954 年)
與自己過去的聯係(約1954 年)
繪畫的空間(約1954 年)
給凱瑟琳·昆的信(1955 年1 月11 日)
給赫伯特·費伯的信(1955 年7 月7 日)
給赫伯特·費伯的信(1955 年7 月11 日)
給勞倫斯·卡爾卡尼奧的信(1956 年)
一則筆記:摘自塞爾登·羅德曼與羅斯科的對話(1956 年)
給赫伯特·費伯的信(1957 年3 月18 日)
給羅瑟琳·歐文的信(1957 年4 月9 日)
給編輯的一封信(1957 年)
緻普瑞特藝術學院(1958 年11 月)
給伊達·孔彌爾的信(約1958 年)
安樂椅:馬剋·羅斯科,一個憤怒的藝術傢的畫像(1970 年)
給赫伯特·費伯和伯納德·裏斯的信(1959 年6 月11 日)
給艾麗斯·亞瑟和斯坦利·庫尼茲的信(1959 年7 月)
給米爾頓·埃弗裏的信(1960 年)
筆記卡片(約1950 年至1960 年)
給倫敦白教堂畫廊的信(1961 年)
與馬剋·羅斯科的一次談話(1961 年)
給赫伯特·費伯的信(1962 年)
嚮米爾頓·埃弗裏緻敬(1965 年1 月7 日)
給伯納德·雷斯的信(1966 年)
給諾曼·雷德的信(1966 年)
給赫伯特·費伯的信(1967 年7 月7 日)
給赫伯特·費伯的信(1967 年7 月19 日)
給斯坦利·庫尼茲和伊利斯·阿捨爾的信(1967 年)
接受耶魯大學頒贈的榮譽博士學位(1969 年)
馬剋·羅斯科年錶
譯後記
精彩書摘
安樂椅:馬剋·羅斯科,一個憤怒的藝術傢的畫像1959年春天,羅斯科已經非常知名,卻仍舊貧睏。那年,他接到有生以來最大的一筆訂單—一組壁畫—每天工作五到九個小時,八個月以來他從未停歇,疲憊不堪。然而,他並不滿意自己正在創作的作品。六月份的時候,他暫且擱置瞭畫筆,決定去風景勝地散散心。於是,他攜妻子、八歲的女兒,隨旅行團乘美國“憲法號”鐵甲艦(USS Constitution)奔赴那不勒斯。
輪船駛齣紐約的第一晚上,他用過晚餐後,一個人在旅行團酒吧遊蕩,想找個人說話。
後來我纔知道,對他來說交談是必需品,就像呼吸一樣。當時,隻有我還在酒吧。其餘的人都跑到船頂的露颱透風去瞭,他們正依傍著船側的欄杆,相談甚歡。我曾有過一次時間甚久的經驗,此後便總是避開。
透過厚厚的鏡片,羅斯科將酒吧環顧瞭一遍。接著,他以一種獨特的、笨拙的步伐,緩緩地朝我走來。他介紹瞭自己,之後就開始瞭我們之間斷斷續續的、不太頻繁的交流—直到上周二他自殺,我們的交流纔終止。我與他最後一次見麵和他死去的日子,相隔瞭七年。期間,我常想,我們隨時可以彼此碰麵,而那些曾經斷掉的話題,他也會隨時撿起,繼續討論。所以,聽聞他去世的消息,我愕然,悵然若失,仿佛聽一個故事,於最關鍵處被打斷,再也無法完結。
當時,我們在船上的酒吧偶遇。最初的幾分鍾裏,羅斯科小心翼翼地試探我是否對藝術界的事情有所耳聞。隨後,他確定我完全置身事外—那些流行的藝術傢、評論傢、畫商、美術館策展人,我一個都不認識。他便鬆瞭一口氣,自由而隨意地嚮我暢談他的作品。後來,他告訴我他從未這樣放鬆過。假如我和藝術界的行傢有哪怕一丁點兒聯係,他都不會如此。因為他不相信那種人。
我也從未見過像他那樣的人。所以,午夜過後很久,我纔返迴我的頭等客艙,把他所講的東西都寫瞭下來—正如隨後的任何一次交談,我都有記錄。現在,我把其中的一些謄寫齣來,希望能給當代藝術的曆史提供一些有用的注腳。
羅斯科曾接受位於西格拉姆大廈(Seagram Building)裏一所極為昂貴的餐廳的委托,托他為餐廳的牆壁創作一組大型壁畫。他第一次提到這件事的時候,說道:“紐約最闊綽的雜種們常去那兒吃飯、炫耀。”
“我再也不會忍受如此的工作瞭,”他說,“繪畫不該放在公共場所被展示。這個工作真的極具挑戰性,我接受是因為我懷著絕對惡毒的意圖—那些婊子養的雜種常去那兒進餐,我要畫的東西一定能搗毀他們的胃口。到時,假如餐廳拒絕把我的畫懸掛在那麵牆上,就是對我最高的禮遇。不過,他們不會那樣做。現在的人們可以忍受任何事情。”
為瞭達到他想要的一種壓抑的、暴虐的、沉重的效果,他正在用一種“黯啞的色調,比我之前用過的任何色調都更加黯淡”。
“畫瞭一段時間之後,”他說,“纔發現無意識中,我受到瞭米開朗基羅(Michelangelo)的那麵牆的影響。他那麵牆在佛羅倫薩美第奇傢族圖書館裏麵的一個樓梯間裏。他畫齣瞭我後來纔理解的一種感覺—讓觀眾産生一種幻覺,他們感覺自己被睏在一個房間裏,所有的門窗都用磚堵死瞭。唯一能做的事情是不停用頭去撞牆。”
“到現在為止,為瞭西格拉姆的工作,我畫瞭三組畫。第一組齣來後感覺不對頭,隨後就把它們分成單幅賣掉瞭。進行第二組的時候,我抓住瞭基本的想法,但每當我獨自一人麵對那些畫時,就忍不住一遍又一遍地修改。我想,我是怕它太過鮮明。我意識到自己的偏差後,又重新開始,這一次我試著緊緊抓牢最初始的想法—那個惡毒的念頭一直在心中盤鏇,從未間斷過。它成瞭強烈激發我的動力,不停催促著我。我想這次旅行過後,等迴到傢,我很快就能完成這組壁畫。”
結果他並沒有完成那組壁畫,它們也沒有齣現在他無比鄙視的那所餐廳的牆麵上。
他尖銳猛烈的言辭很難被當真,因為羅斯科看上去和惡毒毫不沾邊。當時,他正津津有味地啜飲一杯混有蘇打水的威士忌。他的臉飽滿而發亮,有一副男人該有的圓渾的體格。他喝酒的時候,滿懷愉悅,說話的聲音聽起來很輕快。無論在哪裏,我從未見過他發齣一丁點兒憤怒的信號,那時沒有,後來也沒有。他對瑪爾—他的妻子,還有凱蒂—他的女兒,他對她們的感情令人動容。他對待朋友,在我認識的人裏,幾乎沒有人比他更友善,更替彆人著想。然而,據我所知,他的內心深處確實滋生有根深蒂固的憤怒,包裹在一個很細微、很固執的殼裏。他的憤怒不針對任何具體的人和事,而是針對世界普遍性的悲慘境遇,以及將這種悲慘施加給藝術傢的厄運。
他的憤怒是在一段很長的時間裏逐漸滋生齣來的。他還是一個小男孩的時候,就從波蘭移居到瞭俄勒岡。他的父親是一名藥劑師。羅斯科十歲那年,他們從俄羅斯搬走瞭。年少時的羅斯科從未寬恕過他動蕩不安的移居生活,在一片新的土地上,他完全沒有傢的感覺。盡管羅斯科很少講到他的父母,但從我搜集到的資料來看,他們與很多當時的俄羅斯移民一樣,是政治激進主義者。無論如何,羅斯科曾說:“在我能夠全麵理解政治到底牽連著什麼之前,很長一段時間裏,我都是一個無政府主義者。”
“我讀小學的時候,”他說,“我聽愛瑪·戈德曼(Emma Goldman)的課,還聽來自世界産業工人組織(IWW)的演說傢的講座,他們幾乎知道那些天發生在西海岸的所有事情。他們天真的、孩子般的看法令我著魔。後來,大概在二十歲的某個階段裏,我對進步和改革徹底失去瞭信心。我所有的朋友也是。也許是因為庫利奇和鬍佛時代(Coolidge and Hoover era),一切都看上去都像凍僵瞭一般毫無希望,我們就陷入瞭幻滅。但我仍然是一個無政府主義者。這還用問嗎?”
八天的旅途中,我試探性地評論瞭幾次時政,就被羅斯科認定為艾德萊·史蒂文森的狗腿子和傳聲筒。羅斯科絲毫沒有掩藏他的厭惡。慢慢地,一個神父加入瞭我們,約瑟芬·莫迪(Joseph Moody)神父。基本上每個晚上他也會躲進酒吧裏。羅斯科直接宣稱,正規的宗教令他厭煩。這樣,談話總是很快就轉移到他的藝術世界,圍繞著他的敵人蔓延開來。
下麵就是關於羅斯科的一些評論:
“我憎惡、懷疑所有的藝術史學傢、藝術史專傢、藝術評論傢。他們是一群寄生蟲,以藝術的軀體為食。他們的工作不僅毫無用處,更是誤導。他們不會說任何值得聽的話,隻會談論令人著迷的私事緋聞。”
他尤為憎恨兩個人:艾米麗·格瑙爾(Emily Genauer)和哈羅德·羅森伯格(Harold Rosenberg)。
艾米麗·格瑙爾在《紐約先驅論壇報》 (New York Herald Tribune) 寫瞭一篇評論,認為羅斯科的繪畫的本質是“裝飾性”,這是對他最終極的羞辱。哈羅德·羅森伯格則傲慢自大。
“哈羅德·羅森伯格,”羅斯科說道,“總是強迫自己闡釋那些他並不能理解,也無法被闡釋之物。一幅畫不需要任何人去闡釋它到底在錶達什麼。最好的狀況是繪畫自己為自己說話,一個評論傢企圖附加給繪畫某種看法,是一種傲慢的冒犯。”
我想羅斯科也許恰好讀到瞭3月28日哈羅德·羅森伯格發錶在《紐約客》(The New Yorker)的評論。他悲哀地將羅斯科的繪畫闡釋為一個核心事件。
對於藝術評論傢,羅斯科憎惡地說:“整個程序的運轉都是為瞭藝術的普及化—大學、廣告、博物館,還有57大街的銷售員。”
“一群人觀看一幅畫是一種褻瀆,我相信一幅畫隻能單獨和一個不同尋常的人直接交流,那個人恰好和那幅畫、畫傢處於一個頻道。”
齣於這個原因,他基本上不會參加群展。(我猜測,這也是因為他不願意和那些他看不上的藝術傢集體展齣作品。)盡管現代藝術博物館一直在他譴責的名單裏,但他還是在考慮博物館為他舉辦個展的計劃。
“我必須解釋清楚這件事,”他說,“他們需要我,但是我不需要他們。這個展覽會給他們帶去尊嚴,但是不會帶給我。”
為什麼他要如此挖苦現代藝術博物館?“它沒有信念和勇氣。它不能確定哪些畫是好的,哪些畫是不好的。為瞭保險起見,每個藝術傢的作品,它都會買一些。”
然而,1961年在現代藝術博物館為他舉辦的特邀個展上,他並未錶現齣一絲不快。因為他在所有的社交場閤裏,都是羞於錶達的。並且,自從他到瞭每畫必展的階段,他就陷入恐懼和痛苦的暗夜裏瞭。後來,客人們接踵而至為他道賀,對他的繪畫錶示虔敬的贊美和欽佩。他就鬆瞭一口氣,並且親切和藹地和每一個人交談,即便是策展人和評論傢。他和彆人一樣有著自尊心,尤其當他麵對緻敬的時候,沒有什麼不同。
那次旅途中羅斯科對自己繪畫的態度,和後來我們通信中的態度,會偶然齣現一些令我錯愕的矛盾之處。他堅持認為一幅畫應當隻能被放在他傢裏,在那個私密空間裏,被一個真正能欣賞它的“不同尋常的個人”細細品味。後來,至少在他變得很知名的那個時期,他的畫都那麼巨大、昂貴,所以隻能在博物館展齣,除非他的傢擁有昂貴的展覽空間。作為一個無政府主義者,他不支持富人,質疑他們的品位,但是他的畫必然會落在他們手裏。還有,他更多的時候會強調“沒有一幅畫能夠自我評價”。他認為藝術傢所創作的所有作品都是持續性進程裏的一小部分,隻有全部的作品纔能被視為一個單獨的整體。我認為這種觀點暗示博物館與私人收藏的數量必須相當巨大,必須關注一個藝術傢持續不斷的展覽,收藏他最核心的成係列的作品。其中也許潛伏著一些矛盾之處,但是我們不要介意,任何人都沒有權利要求一個藝術傢必須始終如一。
有一次,我嚮他提瞭一個愚蠢的問題:他認為他的繪畫值多少錢?
“我的畫價可以支撐起我的一切,”他迴答說,“十五年前,我必須特彆走運纔能賣掉一幅畫,大約六十美元。現在我的畫價是六韆美元,甚至更多。明天也許就是六百美元。”
羅斯科像大多數人一樣,成長於經濟大蕭條時期,在很長一段時間裏,他們工作的報酬極低。所以,他們對金錢的價值極為敏銳,羅斯科也不例外。1961年的一天,我和我的妻子受邀去他的公寓共進晚餐,晚餐前我們在他工作室碰麵,喝瞭一點酒。他的工作室位於保利街,曾經是一個健身房,也是基督教青年會的會場,後來他把它改造成瞭畫室。他在裏麵竪起瞭一個腳手架,它和西格拉姆大廈裏麵的餐廳的尺寸完全一緻。我們推測那是為瞭創作那組壁畫。那時,他仍然沒有創作齣令他自己滿意的作品,我們拜訪他的那天,他並沒有進行壁畫創作,而是在其他的畫布上進行創作。那是一幅典型的晚期作品:一個大約9×14英尺的矩形,被一種堅實的顔色充滿。在它之上,漂浮著三個呈互補色的稍小尺寸的矩形。
“這種設計也許看上去很簡單,”他說,“但是為瞭達到一種恰到好處的比例和色彩,我會用很長的時間。所有的因素都必須協調一緻。在內心深處,我頗像一個水管維修員。”
那個巨大的腳手架被擱置在一旁,它鄰近的角落,很明顯是曾經的更衣室,裏麵堆滿瞭特彆巨大的畫作,粗略地算一下,大約有八十四幅畫。“現在我沒有錢讓它們進入市場,”他說,“今年我已經支付瞭巨額的所得稅。如果我的畫價能夠保持穩健,明天我就可能賣得更多一些。”
他補充說,他有一點擔心,他的畫是否能夠長久地保持穩健的價格。他非常清楚,同時也痛恨一個現象:紐約藝術市場的風潮更迭極為迅速。有時,他談到幾乎每一個藝術傢、每一所藝術院校,都深陷於一場極度的比拼當中。他認為他自己應當被歸於一個群體,其中包括馬瑟韋爾、剋萊因、斯蒂爾、德庫寜,他敬重裏麵的每一個人。但是他瞧不起康定斯基和本·沙恩,稱他們為“廉價的推銷員”。
“沒有人能夠否認,”有一次他說道,“我們這個群體完成瞭一個使命:摧毀立體主義。現在沒有人再畫立體主義的繪畫瞭。但是我們沒有摧毀畢加索,他仍然具有意義。”
我忍不住問他,他是否考慮過,年輕的藝術傢裏會有誰最終將推翻羅斯科。他說:“如果我知道的話,我會殺瞭他。”聽上去,就像他真的會那樣做。
過瞭一會兒,他補充說那個毀滅者遲早會來,對此他絲毫沒有懷疑過。“如今的國王被弑,就像當初他弑君的方式一樣,弗雷澤的《金枝》(Golden Bough)裏就是這樣講的。”
根據羅斯科的描述,他是偶然間變成瞭一個畫傢。1923年他從耶魯輟學,做過兩年的自由藝術,然後就漫無目的地到瞭紐約,那時他也不清楚自己要做些什麼。
“忽然有一天,”他說,“我偶然闖進一間藝術教室,教師是我的一個朋友,他正在講課。學生們則對著裸體模特畫素描。我就決定要用一生去畫畫瞭。”
在一段不長的時間裏,他曾在紐約藝術學生聯閤學院參加瞭馬剋斯·韋伯(Max Weber)的課程班。後來,他對畫裸體模特産生瞭厭倦,就開始瞭自己的探索之路。有一些年,他畫現實主義繪畫,還有一些被後來的評論傢稱為錶現主義和超現實主義傾嚮的繪畫。這些探索道路沒能讓羅斯科變得有名,也沒有讓他變得富有。在低潮期,有兩年的時間,他的工作是紐約的WPA聯邦藝術項目(WPA Federal Arts Project)。大約在1947年的時候,他發展齣一種繪畫風格,引起瞭重量級的評論傢和贊助人的注意。佩吉·古根海姆(Peggy Guggenheim)就是其中之一。緊接著,他的繪畫特色—矩形塊麵漂浮於色域—逐漸培養起他的繪畫市場。最初是通過貝蒂·帕森斯(Betty Parsons),後來是西德尼·詹尼斯畫廊(Sidney Janis Galleries)。一直到60年代早期,他被公認為美國最傑齣的六位畫傢之一。
我的妻子曾經告訴他,他一定是一位神秘主義者。因為在她看來,他的繪畫傳遞給她一種巫術和儀式的感覺,近乎一種宗教性。對此,他否認。
“不是巫術。也許是先知。但是我絕非預言即將來臨的睏境。我隻是將目前的睏境畫齣來。”
在他未完成的西格拉姆的壁畫裏,我能看到他的所指。在後來的階段,大量的色塊—紫色的、黑色的,還有像凝固的血跡一樣的紅色—散發齣明顯的死亡的感覺。雖然他否認過,但還是流露齣一股宗教的神秘主義。現代藝術博物館的彼得·塞茲(Peter Selz)將其描述為“對文明之死的歌頌……它們的主題可能是死亡和古典主義的復活,不是基督教的神話,而是麵對死亡,一種現代主義的舞蹈”。
最後,羅斯科很明確地得齣瞭相近的結論。羅斯科決定將那組已經投入瞭大量心血和情感的壁畫,變成一筆好的交易,而不是對那些進行饕餮大餐的富豪錶示齣厭惡的姿態。甚至它值得被安置在一個比富豪常常光顧的餐廳還要好的環境。在他死前不久,他已經準備把它們掛在一個專門為瞭那組畫而建的地方—休斯敦的一座不舉辦任何宗教活動的小教堂裏—德·梅尼爾(de Menil)傢族按照羅斯科的規定和委任所建的教堂。
我隻聽到過兩次,他暗示他的作品可能是他埋藏於內心的宗教衝動的錶達。
在1959年旅途結束前的幾天裏,我們兩個傢庭在那不勒斯及周邊參觀瞭多處景點,有時候一起,有時候分開。他參觀完龐培古城後,對我說他感覺在他的作品和龐貝神秘之屋裏的壁畫之間有一種“強烈的親密關係”—“同樣的感覺、同樣的陰鬱色彩的擴散性”。
我們兩個傢庭一起進行瞭一整天的帕埃斯圖姆(Paestum)探險。帕埃斯圖姆是古希臘殖民地的一處遺址。裏麵有三處早於雅典時期的神廟廢墟。(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帕埃斯圖姆被美國軍隊攻下,作為薩勒諾[Salerno]灘頭堡的一部分。海神尼普頓[Neptune]神廟被強占為總部和通訊中心,位於戰場附近的一群小山當中,它沒有被德國炮兵部隊摧毀,簡直是一個奇跡。)
在一個清晨,我們於那不勒斯乘火車朝南部齣發。兩個意大利的高中男孩,齣來過暑假,他們和我的女兒年齡相仿,偶遇熟識,便立刻決定加入我們的旅行。他們說很願意作為東道主招待我們—盡管雙方的見麵有些尷尬,他們不會講英語,我們當中沒有人會講意大利語。我們隻有用法語進行群體性的對話,他們並不擅長,而我的大女兒妮可(Nic)竭盡全力也隻是會一點點。
最終我們見到瞭神廟的廢墟,之前我們在指導手冊上見過它的圖片,它比我們所期待的更加令人敬畏。整個早晨,我們在其間穿梭。羅斯科一臉茫然地對著每一處建築的細節進行研究,幾乎沒有說一句話。中午的時候,我在附近的雜貨店買瞭一些麵包、奶酪,還有一瓶葡萄酒。在赫拉神廟裏的一個陰涼處,我們一起進午餐。妮可幾乎沒有吃一口,她一直在忙著解釋那兩個男孩的問題。那個時候,我們是誰?我們在那裏做什麼?
她對羅斯科說:“我告訴他們,你是一個藝術傢。他們問你是不是來畫這座神廟的。”“告訴他們,”羅斯科說,“在我不知道這座神廟之前,我一直都在畫希臘神廟。”
我猜測羅斯科的死亡和一個事實相關:那些年,藝術傢畫神廟並不是一件值得鼓勵的事情。當然,這隻是純粹的臆測。
在幾個世紀裏,那是藝術的一個主要的功能。在龐培的神廟,以及後來拜占庭和歐洲的教堂、廟宇裏,藝術都和宗教緊密相關。中世紀和文藝復興時期的最傑齣的藝術傢都緻力於嚮文盲傳授《聖經》故事,藝術手法有濕壁畫、馬賽剋繪畫、肖像畫、雕塑、彩色玻璃—他們所在時代的視覺的教具。教會是藝術傢最重要的贊助人。他們的社會角色既明確又安穩,他們的工作是必不可少的,也是尊貴的,實際上,近乎神聖,被視為上帝的工作。
隨著印刷機的發明和宗教的衰落,以及最後照相機的齣現,這個功能被逐漸消解瞭。到瞭20世紀,藝術傢不再扮演獨一無二的角色:圖像的創作是為瞭滿足藝術傢自身文化的強烈需求,他們自己都能獨立地完成。不可避免地,很多人開始將其作品作為一種“本質的裝飾性”—社會的裝飾品,而不是靈魂的食糧。
最近,藝術傢仍被歸屬為一種更加卑下的角色:被藝術界所開掘的一個構件。藝術界指的是由藝術經紀人、評論傢、時髦的收藏傢、藝術投機商共同構成的世界。甚至最近,有一個共同的投資機構開始計劃投入藝術基金,介入藝術機製。機構管理者很明顯對藝術傢不感興趣,他們隻關注藝術傢的增值潛力。沃霍爾的作品會不會比羅斯科的作品升值更快?
這樣的問題會激怒像羅斯科一樣的人。像約翰·卡納迪(John Canaday)那樣的評論傢的判斷同樣也會激怒羅斯科。他針對羅斯科在現代藝術博物館的展覽寫瞭一篇文章,他極力強調:“如今,藝術傢的工作就是為評論傢對美學進程的探索提供材料。盡管這是一種本末倒置的關係,但是仍然具有閤理性。毫無疑問,如果某一天其他的藝術形式可以取代繪畫,基本滿足所有的需求,那麼繪畫所剩下的功能就更加萎縮瞭。在這種情況下,評論傢自然而然會想在畫傢中間尋找說得最少的那個,因為那個畫傢為美學手法留下瞭更多的空間。”
我相信,羅斯科痛恨於被強行歸入某種材料提供者的角色—不管是為瞭投資信托,還是為瞭美學實驗。我已經聽說過一些關於他自殺的解釋—他的身體不好,或者他最後六個月失去瞭創作力,或者藝術界將興趣轉移到更年輕的下一代而將他拋棄瞭。可能在其中存在某些原因,我不知道。我的直覺告訴我,至少有一個原因是他長期以來的憤怒,一種閤理的憤怒:當一個人感覺自己應當命定去畫神廟,卻發現自己的作品隻能被當做交易的商品。
前言/序言
導 言今天,馬剋·羅斯科(1903—1970)被視為20世紀最具影響力、最重要的藝術傢之一。在他死後的三十六年裏,藝術界與齣版界從未消減過對其作品的關注度。1998年,華盛頓美國國傢藝術博物館與惠特尼美術館為他舉辦的大型迴顧展令其眾多藝術追隨者精神振奮。然而,作為20世紀最富爭議的、展覽次數最多的藝術傢之一,羅斯科所撰寫的文章卻未得到相應研究。直至20世紀末,現有關於其寫作的齣版物,僅有馬剋·羅斯科基金會的會長邦妮·剋裏爾沃特(Bonnie Clearwater)所編輯齣版的12篇文章。甚至,這12篇文章的讀者僅限於羅斯科的研究者。
羅斯科的同時代人,譬如羅伯特·馬瑟韋爾、巴內特·紐曼、萊因哈特,他們同為紐約畫派的成員,且同樣進行著著作頗豐的寫作。乖謬之處在於,與他們相比,羅斯科所撰寫的大量文章卻未曾麵世。這加深瞭一個誤解,即羅斯科一生所撰寫的文章與隨筆總共隻有12篇,加之那12篇文章的寫作時間全都處於他進行抽象錶現主義繪畫之前,所以纔會齣現之後他貌似停止寫作的假象。荒誕的是,學術界已有人將這種“寫作的缺失”闡釋為他個人與寫作世界的決裂,似乎他的沉默是他追尋抽象藝術道路的一部分。
事實上,羅斯科一生從未間斷過寫作生涯。2004年,羅斯科手稿集《藝術傢的真實》的公開齣版便是無可辯駁的證據。那部手稿沉寂瞭六十多年後,終得以麵世。本書則將徹底消除人們對羅斯科的誤解—在抽象時期及隨後的時間裏,他並未停止寫作:本書所收錄的文章,約有一半撰寫於1950年之後,正值羅斯科探索抽象繪畫的時期。
羅斯科的寫作彰顯齣他在藝術與哲學領域的深厚學識,這在他的同時代人當中是極為罕見的。重要的是,讀者們發現已齣版的《藝術傢的真實》是一本不摻雜任何個人生活的純理論著作,就像剋裏斯托弗·羅斯科(Christopher Rothko)在該書的導論裏所強調的,他的父親馬剋·羅斯科在該書中從未使用過第一人稱單數代詞“我(I)”。約1940年左右,羅斯科曾圍繞具象藝術的局限以及嚮抽象藝術轉變的問題寫過文章,之後不久其藝術道路便齣現瞭重大的突破。其著作《藝術傢的真實》曾為這一關鍵時期提供瞭證據。關於此關鍵時期的轉變,本書裏也有所提及:
關於這一階段(具象階段)的作品,1939年巴內特 ·紐曼在他的畫廊為我做瞭最後一次相關展覽。此後不久,我意識到齣於個人的素養和偏好,導緻瞭錶達傾嚮的局限性。我停止瞭繪畫,用瞭將近一年的時間進行寫作,斟酌關於神話和野史的一些想法。這是我如今作品的基礎(超現實主義階段,從1941年至1947年)。
1930年代末到40年代初,紐約畫派的成員們開始接觸那些“二戰”期間從歐洲流亡至美國的先鋒派藝術傢。在與他們進行交往、思考、學習的氛圍當中,羅斯科於1939年至1941年間完成其著作《藝術傢的真實》。他的繪畫風格也隨之發生瞭轉變,從具象走嚮超現實。此後,羅斯科不再畫人物形象,他想錶達一種象徵:
我這一代人沉迷於人物形象,我曾習得此類技法。那是一種極為勉強的方式,我知道那並不能完成我的需要。不管是誰使用瞭那種方式,都是在打破它。沒有人能夠畫齣如其所是的形象,也沒有人會自詡他筆下之物能夠錶達整個世界。有一段時間,我用神話取代瞭各種各樣的生命體,盡管那些有生命之物可以毫不羞赧地擺齣各種強烈的姿態。我開始采用帶有形態感的形式,通過它們,我可以畫齣人所不能達到的姿態。
羅斯科重新定義形式、空間、美、抽象、神話等觀念,他認為繪畫像音樂與詩歌一樣,擁有著相同水準的強度和情感。因此,他重申“詩同畫(ut pictura poesis)”的靈感基礎,認為自文藝復興時期便開啓瞭偉大繪畫的先河。在此意義上,其著作《藝術傢的真實》亦可被視為“最後一位古老大師”的作品。
羅斯科原名馬庫斯·羅斯科維茲(Marcus Rothkowitz),1903年齣生於俄國的德文斯剋(現為拉脫維亞的陶格夫匹爾斯市)。其父雅各布·羅斯科維茲(Jacob Rothkowitz)是一名藥劑師,馬剋·羅斯科在傢排名第四,是最小的孩子。在他10歲那年,全傢移民美國,定居在俄勒岡州的波特蘭。羅斯科曾在耶魯大學就讀過兩年,當時他想要做一名律師或者工程師。1923年,他放棄學業移居紐約。在紐約,他拜馬剋斯·韋伯(Max Weber)為師,韋伯指導他學習設計與繪畫的課程,並建議他學習塞尚(Cézanne)。隨後,羅斯科結識瞭畫傢米爾頓·埃弗裏(Milton Avery),1928年他們一起舉辦瞭聯展,那是羅斯科人生首次參加展覽。1929年美國步入經濟危機,羅斯科開始在布魯剋林猶太學院給孩子們講授設計與繪畫課程。這段獨特的教學經曆一直持續瞭二十多年之久,期間的很多瑣事成為激發他早期寫作的靈感。1933年,他在波特蘭的當代藝術博物館與紐約的當代藝術畫廊(Contemporary Art Gallery)舉辦瞭首次個展,這標誌著他畫傢生涯的正式開始。1930年代,他傾嚮於錶現主義繪畫,在一些室內畫與城市風景畫題材上錶現得尤為明顯。40年代,他步入瞭新的階段,開始進行超現實主義繪畫。在此階段,人物形象逐漸消失,大量以神話與自然為母題的繪畫齣現。1945年他首次在佩吉·古根海姆畫廊(Peggy Guggenheim’s Gallery)舉辦展覽,1946年與貝蒂帕爾森畫廊(Betty Parson’s Gallery)簽約。
羅斯科藝術生涯的第二個重要的轉摺點發生在1947年。為瞭追求永恒性,羅斯科用抽象的形式“取代”瞭超現實主義題材,即他所命名的“復閤形式(Multiforms)”。1948年,他與羅伯特·馬瑟韋爾(Robert Motherwell)、威廉·巴齊奧蒂(William Baziotes)、戴維·黑爾(David Hare)共同創辦藝術傢主題學校。1954年,羅斯科與辛德尼·傑尼斯畫廊(Sidney Janis Gallery)簽約。十年後,他開始在馬爾伯勒畫廊(Marlborough Gallery)舉辦展覽。1968年,羅斯科患上破裂性動脈瘤,此後他的醫生禁止他創作高度超過40英寸的畫。1969年,他接受耶魯大學頒發的榮譽博士學位。1970年,羅斯科在紐約的工作室自殺。一年後,梅尼爾傢族(Menil Family)齣資建立“羅斯科小教堂”以紀念他。
這本書所收錄文章數量將近90篇,全部創作於1934年至1969年期間(羅斯科首次舉辦個展後一年至他離世前一年),記錄瞭羅斯科整個藝術生涯與美學思想的發展軌跡。這些隨筆,作為羅斯科其人及繪畫生涯的碑銘,構成瞭他兼具智性與感性的自畫像。
本書第一篇文章作於1934年,題為《教導未來藝術傢和藝術愛好者的新方法》。在文中,羅斯科講述瞭他在布魯剋林猶太學院的教學經驗,關於兒童藝術經驗的分析激發齣眾多問題:譬如,兒童與精神病患者之間是否具有類似的藝術態度?不清晰、慣有的感知技法是如何嚮藝術傢傳遞視覺意義的?此外,作為教育改革的擁護者,羅斯科不斷追問藝術教育的有效性。本書最後一篇文章作於1969年,是他接受耶魯大學頒發的榮譽博士學位時的演講。經考察現存資料發現,此篇演講是他生前最後一篇文章,在其離世前幾個月曾反復修改。本書所收錄文章的時間跨度從1934年至1969年,包含有羅斯科曾公開發錶於雜誌、期刊、展覽目錄的所有資料,他與紐約畫派藝術傢、曆史學傢、畫廊負責人、美術館策展人之間的重要通信,以及一些筆記、演講、訪談的轉錄文獻。
這些文獻為我們提供瞭一條理解羅斯科生活與藝術的敏銳途徑。他所撰寫的文章為我們展現齣他繪畫生涯的藝術探險—在其著作《藝術傢的真實》裏所呈現齣的純理論式的藝術觀念,以及本隨筆集所呈現齣的一種實踐化的、體驗式的、個人化的認知,均有所體現。剋裏斯托弗·羅斯科曾提及其父羅斯科在《藝術傢的真實》一書裏從未以作者“我”自居,也從不談論自己的繪畫。但在本書所收錄的每一篇文章裏,羅斯科都在討論自己的藝術。
有一個事例便能清楚地證明這種“自我寫作”的特質。1940年代中期,羅斯科的繪畫齣現瞭一次重要的變化,他摒棄瞭超現實主義的風格,進入“復閤形式”的抽象繪畫,即抽象錶現主義之前的階段。為瞭尋求一種更為純粹的象徵主義的形式,羅斯科於1945年給巴內特·紐曼寫信說道:“現在的問題是把象徵進一步具體化。這令我很頭痛,但也使繪畫工作變得極為振奮。遺憾的是,我們無法一步就抵達預期的終點。在道路還未明晰之前,必然要忍受接二連三的失敗。”
在另一封給加利福尼亞藝術學院(California School of Fine Arts)教授剋萊·斯龐(Clay Spohn)的信裏,羅斯科也曾錶示他正全心投入到這一轉變:“這次的繪畫探索過程,齣現瞭一些前所未見的元素,我必須繼續探索下去。如今,它們不斷地刺激著我,給我一種幻覺,至少我不會再用明年的時光重復過去一年的感覺。”
羅斯科的整個藝術生涯都在進行探索性的個人實驗。本書所收錄的大量隨筆顯示其藝術主題之間存在一些互相抵牾之處,然而希爾頓·諾德曼認為貫穿整本文集的核心思想仍具有某種統一性:幸好有這些隨筆,讓我們看到成熟的理性思考與最原始的想法之間産生瞭碰撞。支撐羅斯科全部作品的精神性追求構成瞭他的藝術觀念,他把藝術上升至像神話、戲劇、傳說一樣的精神性存在。他終其一生都在探尋永恒的象徵物。
從某種角度看,這些隨筆可以分為四大部分:
第一部分是羅斯科寫給同時代藝術傢的書信集,譬如紐曼、赫伯特·費伯、埃弗裏、馬瑟韋爾、斯坦利·庫尼茨等人。無論是身處紐約,還是在美國境內旅行,或遠行歐洲,羅斯科都會給朋友們寫信。這些信件談及他所關心的藝術問題,並為我們勾勒齣一個更加私密的羅斯科。作為一手文獻,這些隨筆描繪齣羅斯科的生活,以及他與同時代藝術傢之間的友誼。
第二部分涉及與美術館、藝術展覽相關的事宜。羅斯科多次緻信策展人、美術館館長,細聊關於策劃、布置展覽在內的每一件瑣事。他與藝術評論傢、策展人凱瑟琳·昆之間的通信尤為有趣。1954年,凱瑟琳·昆提議在芝加哥藝術學院為羅斯科做一場個展,那將是他首次在重量級美術館舉辦的個展。在一次偶然的通信過程中,凱瑟琳·昆提及想要發錶一組以“羅斯科訪談”為主題的文章。雖然這項計劃後來並未實現,但所幸羅斯科寫給凱瑟琳·昆的13封信件被保存瞭下來。在通信過程中,他們討論過布展問題,以及凱瑟琳·昆所提齣的一些純理論的藝術問題。那些從未得以麵世的通信,如今作為原始文獻揭示齣羅斯科是如何對待自己的作品的。
第三部分涉及藝術教育問題。羅斯科從始至終都在關注教育問題,他早期寫於1934年的一篇名為《塗寫本》的隨筆,以及其著作《藝術傢的真實》都是有力的證明。從1940年代末開始,他相繼在幾所大學任教。
第四部分涉及羅斯科如何逐漸形成“藝術作為交流”的觀念。大量的文獻證明,尤其自1950年代以來,當藝術作品與觀眾之間的移情成為羅斯科藝術理念的一個核心要素時,他便秉持藝術作為交流的途徑而存在。他對這種美學理念的堅持與其抽象錶現主義風格的作品契閤一緻,他的繪畫逐漸轉變成與觀眾進行交流的現場。1958年,他在普瑞特藝術學院做瞭一場演講,他用“假象(facade)”形容自己的作品:“我的繪畫確實是假象(正如它們曾被認為的那樣)。有時我會打開一扇門,一扇窗,或者兩扇門,兩扇窗。這隻是一種精明的、敏銳的策略。隻透露一點點,比和盤托齣更有力量。”
羅斯科堅信藝術作為交流、作為對話而存在。他認為繪畫位於畫傢與觀眾之間,創造齣一個用以互相交流的想象空間,正如一篇隨筆裏所寫:繪畫總是“把你拉進來”。倘若我們細讀本書,就會置身於這種交流空間。
米格爾·洛佩茲·萊米羅
2005年10月31日
用戶評價
坦白說,我一直對那些將藝術傢的生平與創作割裂開來的論述感到不滿。藝術傢的創作過程,本質上就是他們生命曆程的物質化體現,是他們與周遭世界不斷對話、衝突和融閤的産物。因此,我熱切期盼這本書能提供一個清晰的綫索,追蹤羅斯科從早期的超現實主義探索,到最終確立他那標誌性的矩形結構和模糊邊界的風格轉變軌跡。我想要知道,是哪些社會思潮、哲學理念,或者更私密的個人經曆,推動他做齣瞭如此決絕的風格轉嚮?那些被評論傢津津樂道的“神聖的悲劇感”,究竟是如何在1934年到1969年這關鍵的三十多年間,通過筆觸和顔料的堆疊逐漸凝練齣來的?我尤其好奇,在那個藝術界風起雲湧的年代,他如何看待學院派的束縛,又是如何與同時代的其他巨匠們進行無形的較量和緻敬的?這本書如果能細緻勾勒齣他思想的“骨骼”與“血肉”,而不是停留在對作品錶麵的美學分析上,那它就成功瞭。它應該是一部充滿內在張力的個人史詩,而非枯燥的學術論文集。
评分閱讀藝術傢的隨筆,最忌諱的就是那種故作高深的腔調,讓人感覺像在啃一塊乾燥的、沒有水分的知識。我更傾嚮於看到一種近乎坦誠的、甚至是略帶挫敗感的記錄。羅斯科無疑是那種極度重視作品體驗的藝術傢,他不斷強調觀眾需要被作品“籠罩”,需要進行一種近乎宗教般的沉浸式接觸。我希望在這些隨筆中,能捕捉到他對於這種理想觀賞狀態的執著追求,以及在現實中實現這種狀態的種種睏境。想象一下,他是否會在字裏行間流露齣對大眾無法理解其深意的無奈?他是否會記錄下對那些隻注重裝飾性或投資價值的收藏傢的復雜情緒?這種“藝術傢與世界之間,尤其與市場之間的張力”,往往是理解一位偉大創作者內心世界的關鍵切口。如果隨筆能透露齣他對自己作品最終命運的憂慮,或者對藝術在消費主義時代如何自處的深刻反思,那麼這本書的價值將大大提升。我期待的是那種能夠讓人感同身受的、創作中的“人性掙紮”。
评分從書名中限定的時間跨度(1934—1969)來看,這幾乎涵蓋瞭羅斯科藝術生涯最核心、最富有創造力的階段,也包括瞭二戰後美國藝術中心地位的確立,以及他個人聲名鵲起的全過程。我非常關注他在不同曆史時期的心態變化。1930年代,麵對全球性的危機和個人身份的探索,他的藝術語言必然帶有某種探索的彷徨與批判性;而進入戰後,當他被推上“美國藝術領袖”的位置時,他的責任感和自我要求又會發生怎樣的微妙變化?我希望通過這些文字,能構建齣一個動態的羅斯科形象,而非一個靜止的符號。尤其是在他晚期為德剋薩斯教堂設計的那些作品時,那種對“黑暗”和“終結”的探尋,必然伴隨著極其深刻而私密的哲學思考。這本書若能精準捕捉到這些時間節點上的思想波動,並將其與當時的藝術環境相對照,那便是一部富有洞察力的編年史,遠超瞭一般的“迴憶錄”範疇。
评分讀完這本書,我最希望獲得的,是一種在精神層麵上被“淨化”或“洗禮”的感覺。羅斯科的畫作,往往被形容為能引發觀者一種崇高而近乎冥想的狀態,這種狀態是刻意營造齣來的,而非偶然發生的。那麼,他是如何指導——或者說,是如何“命令”——觀者進入這種狀態的呢?他的隨筆無疑是理解他“劇場化”創作理念的最佳途徑。我期待他能闡述那些看似簡單的色塊構圖背後,所蘊含的對空間、光綫、以及人與作品邊界的精確計算和控製。這不應是關於繪畫技巧的探討,而更應是關於“體驗設計”的哲學闡述。如果這本書能揭示齣,這位大師是如何將畫布變成一個能夠容納人類全部情感重量的“容器”,並且清楚地告知我們如何正確地“進入”這個容器,那麼這本書就成功地完成瞭對藝術本質的終極叩問,賦予瞭我們一種新的觀看世界的方式。
评分這本書的書名倒是挺引人深思的,光是“藝術何為”這四個字,就足以讓人在書店裏駐足良久,心裏琢磨著這背後蘊含的重量。我拿起它,首先感受到的是一種沉甸甸的、仿佛跨越瞭數十年時光的質感。我期待的,不是那種高高在上、生澀難懂的藝術理論灌輸,而是能觸摸到一位大師內心深處最真實的聲音,那種在創作的陣痛與狂喜中迸發齣的思考火花。我希望它能像一把鑰匙,幫我開啓通往抽象錶現主義核心思想的大門,理解那些看似隨機的色塊和光影是如何構建起一個獨立於現實世界的精神宇宙的。想象著羅斯科在那些漫長的工作日裏,是如何與畫布進行一場無聲的搏鬥,如何用色彩來錶達人類共通的情感——那種超越語言的、關於生與死、崇高與虛無的終極追問。這本書如果能將這些點滴的思緒、那些未經修飾的內心獨白一一呈現齣來,那它就不再僅僅是一本關於藝術史的附錄,而更像是一份獻給所有在現代性迷宮中尋找意義的靈魂的宣言。我希望讀完後,我對“觀看”這件事本身會有更深刻的體悟,明白藝術的價值並非在於它描繪瞭什麼,而在於它引發瞭什麼。
評分書非常好,對此非常滿意,非常開心
評分此用戶未填寫評價內容
評分還未看,看上去不錯。
評分書很好 發貨迅速 快遞小哥很好? 贊贊贊
評分看看羅斯科的文字。
評分很好
評分不錯
評分此用戶未填寫評價內容
評分好好的?????,好想去
相關圖書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尋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5 book.qciss.net All Rights Reserved. 圖書大百科 版權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