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具体描述
编辑推荐
大师之作,出手不凡。加缪小说处女作内地首次出版。
加缪终其一生都在思考的问题,可以在这里找到发端与答案。梅尔索(《快乐的死》主人公)的艰困的探索,预告了日后默尔索(《局外人》主人公)的方向。
在一桩精心设计的谋杀案之后,梅尔索获得了人人羡慕的财富,过着财富与时间都有充分余裕的生活。然而,梅尔索仍然不幸福。
一个人如何才能快乐?为什么有了金钱,孤独却并不离开?
内容简介
《快乐的死》为加缪的小说处女作,完成于他二十四岁那年,但直至他去世后才出版。在一桩精心设计的谋杀案之后,梅尔索获得了人人羡慕的财富,过着财富与时间都有充分余裕的生活。然而,梅尔索仍然不幸福。
一个人如何才能快乐?为什么有了金钱,孤独却并不离开?
梅尔索的抉择和省思,也预告了加缪日后的其他小说和论述。
目录
第一部 自然的死第二部 有意识的死
精彩书摘
第一部自然的死
第一章
上午十点,帕特里斯·梅尔索稳步走向萨格勒斯的别墅。这个时间,看护出门买菜,家中无旁人。时值四月,是个明亮而冷冽的美丽春天早晨,晴朗而冰冷的天空,挂着灿烂但毫无暖意的大太阳。别墅附近,山丘上林立的松树之间,清净的光芒顺着树干流泄而下。沿路空无一人。这条路是缓升坡。梅尔索手里提着行李箱,于世间壮丽的这一天踏在冰冷的道路上,在短促的脚步声以及行李箱把手规律的嘎吱声中,他前进着。
快到别墅之前,这条路通达一个设有长椅和绿地的小广场。灰色的芦荟间掺杂着提早开花的红色天竺葵,蔚蓝的天空和涂了白色灰泥的篱笆墙,这一切如此新鲜又动人,梅尔索忍不住驻足了一会儿,才再踏上通往萨格勒斯别墅的下坡小路。到了门口,他停在原地,戴上手套。他打开那残疾人向来刻意开着的门,然后顺势将门关上。他步入长廊,来到左侧第三道门前,敲门进去。萨格勒斯就在里面,两条残腿上盖着一条格子毯。他人在壁炉旁,就坐在沙发上,亦即梅尔索两天前坐的那个位子。萨格勒斯正在阅读,书本放在毯子上。他瞪大了双眼,直盯着现在站在关上了门的门口的梅尔索,眼中丝毫不见惊讶之意。窗帘是拉开的,地上、家具上,以及物品之间,洒落着几摊阳光。窗外,早晨在金黄而冷冽的大地上欢笑着。一股冰冷的喜悦、群鸟不安的嗓子所发出的尖锐叫声,以及丰沛满溢的无情光芒,使早晨显得天真无辜而真实。梅尔索站在那里,房间内的闷热直扑他的喉咙和双耳。尽管气温变暖了,萨格勒斯仍让壁炉燃烧着熊熊烈火。梅尔索感到血液冲上太阳穴,在耳垂怦怦跳着。对方依然不发一语,只以目光注视他的一举一动。梅尔索走向壁炉另一侧的矮柜,不顾那残疾人,径自把行李箱放在桌上。他感觉脚踝隐隐颤抖着。他停下脚步,点了根烟。因为戴着手套,点起烟来不由得有些笨拙。背后传来模糊的声响。他嘴里叼着烟,转过身来。萨格勒斯依然盯着他,但刚把书合上。梅尔索感觉到炉火几近灼痛地烤着他的膝盖。他看了看那本书的书名——巴尔塔沙·葛拉西安所著的《智慧书》。他低头毫不犹豫地把矮柜打开。黑色手枪熠熠发亮,宛如一只优雅的猫镇着萨格勒斯的那封白色的信。梅尔索左手拿起信,右手拿起枪。犹豫了片刻后,他把枪夹到左腋下,把信拆开。里头仅只一张大张的信纸,纸上寥寥几行萨格勒斯偌大刚硬的字迹:
我只不过是灭除了半个人而已。还请见谅。小矮柜里的,用来偿付服务我至今的人员,应绰绰有余。此外,我并希望该笔款项能用于改善死囚的伙食。但我亦深知此乃奢求。
梅尔索一脸肃然,把信纸折好。此时,香烟的烟熏痛了他的眼睛,些许烟灰掉落在信封上。他把信抖了抖,放到桌上显眼的地方,随即转向萨格勒斯。萨格勒斯现在凝视着信封,他短而粗壮的双手搁在书本旁。梅尔索低头转动矮柜里小保险箱的钥匙,从里面取出一捆捆纸钞。纸钞用报纸包裹着,只看得到纸钞的末端。他一手夹着枪,单手将钞票一一放入行李箱。柜里百张一捆的纸钞不到二十捆,梅尔索发现自己带来的箱子太大了。他在柜里留下一捆一百张的纸钞。盖上行李箱后,他把抽了一半的烟扔入炉火,然后右手握着枪,走向那残疾人。
萨格勒斯现在望着窗外。可以听到一辆汽车缓缓从门前经过,发出轻微的磨合声。萨格勒斯一动也不动,似乎正尽情端详着这个四月早晨与人无涉的美感。感觉到枪口抵着自己的右太阳穴时,他并未移开目光。梅尔索望着他,发现他眼里满是泪水。梅尔索闭上了双眼。他后退了一步,然后开枪。他依然紧闭着双眼,靠墙站了一会儿,感觉到耳朵处的血液仍怦怦跳着。他看了看。那颗头倒向左肩,身躯几乎未歪斜,只是萨格勒斯已不复见,只看得到一个巨大伤口上鼓胀的脑浆、颅骨和鲜血。梅尔索开始打哆嗦。他绕到沙发的另一侧,匆忙拿起萨格勒斯的右手,让它握住手枪,把它举到太阳穴的高度,再任它垂落。枪掉到沙发的扶手上,再掉到萨格勒斯的腿上。在这过程中,梅尔索看了看萨格勒斯的嘴巴和下巴,萨格勒斯的表情就和他刚才望着窗外时一样地严肃而悲伤。这时,门外响起一声尖锐的喇叭声。这不真实的召唤又回荡了一次。梅尔索依然低头望向沙发,不为所动。一阵汽车车轮转动声,意味着肉贩离去了。梅尔索拎起行李箱,把门打开,金属门栓被一束阳光照得闪闪发亮。他旋即头昏脑涨口干舌燥地走出房间。他打开大门,大步离开。四下无人,仅小广场角落有一群孩童。他逐渐远离。抵达广场时,他顿时意识到气温的寒冷,身体在薄西装外套下瑟瑟发抖。他打了两次喷嚏,小山谷里回荡起嘲笑般的清晰回音,在清澈的天空中愈送愈高。他脚步有些踉跄,暂时驻足,用力呼吸。从蓝色的天际降下千千万万个白色小微笑。它们嬉戏在仍满是雨水的叶子上、巷弄里濡湿的石板上,飞向鲜红色屋瓦的房舍,再拍翅向上,飞向它们刚刚才从中满溢出来的空气和阳光之湖。在那上方飞行着一架极小的飞机,传来一阵轻柔的隆隆声。在空气如此奔放而天空如此富饶之下,似乎人唯一的任务就是要活着且活得快乐。梅尔索内心的一切静止了。第三个喷嚏撼醒了他,他感觉自己似乎因发烧而战栗着。于是在行李箱的嘎吱声和脚步声中,他未环顾四周便逃跑了。回到家里,他把行李箱丢在角落,旋即躺到床上,睡到下午三四点。
第二章
夏天让港口尽是喧哗和阳光。时间是十一点半。太阳仿佛从中央剖开来,以极其沉重的暑气压迫着码头堤道。阿尔及尔商会的货棚前,一艘艘黑色船身、红色烟囱的货轮正把一袋袋麦子装上船。细微尘埃的芬芳,融入炽热太阳孵烤出来的柏油的厚重气味中。在一艘散发着油漆和茴香酒清香的小船前,一些人正喝着酒,几名穿着红色紧身衣的阿拉伯杂耍艺人,在发烫的石板地上一而再、再而三地翻转身体,阳光也在一旁的海面上跳跃着。扛着货袋的码头工人未理会他们,径自踏上从码头跨向货轮甲板的两块富有弹性的长条木板。到了上方,工人身后的背景顿时只剩下天空和海湾。他们身处在数座卷扬机和船桅之间,停下来片刻,心旷神怡地面向天际,两眼炯炯有神,脸上覆盖着一层白色的厚厚的汗水与尘土,然后才不假思索地潜入弥漫着沸热鲜血气味的底舱。在酷热的空气里,一阵阵尖锐的鸣笛声不绝于耳。
长条木板上,工人忽然停下脚步,乱成一团。他们中的一人跌落到厚木板之间,幸好厚木板排列很密,托住了他。但他的手臂折到了背后,被那袋很重的货物压断了。他痛苦地哀嚎着。这时,帕特里斯·梅尔索从办公室出来了。一到门口,酷暑便令他窒息。他吸入了满口的柏油热气,喉咙像被刮了一般,然后走到码头工人那头。他们已将伤者抬出来,他倒卧在木板和尘土之间,嘴唇因痛楚而发白,手肘上方断了的手臂就这么垂着。一截碎骨从皮肉中穿出,可怕的伤口淌着血。鲜血沿着手臂回旋流下,一滴一滴落在发烫的石板上,发出微小的嗞嗞声,轻烟自滴落处缓缓升起。梅尔索静静不动地望着鲜血,忽然有人拉他的手臂。是埃曼纽,那个“跑腿的小伙子”。他向梅尔索指了指一辆正朝他们开来、引擎发出轰隆巨响的卡车。“走吧?”梅尔索开始奔跑。卡车从他们面前经过。他们立即追上去,很快被淹没在噪音和飞扬的尘土中,气喘吁吁,视线不清,心神的清楚程度只够感觉到在卷扬机和其他机具的狂乱节奏中,自己被狂奔的冲劲带动着,伴随着的还有海平线上船桅的舞动,以及他们经过的有着麻风病皮肤般船身的船的摇晃。梅尔索对自己的体力和弹跳力很有自信,他率先施力,一跃而上;他协助埃曼纽跃上车斗。两人坐下来,垂着双腿。于是在白蒙蒙的尘土、从天降下的光亮暑气、艳阳,和由满是船桅和黑色起重机的港口所构成的巨大神奇场景中,卡车急速远离。行经高低不平的堤道路面时,梅尔索和埃曼纽的身体颠簸不已,他们笑得上气不接下气,一切都让他们感到迷炫。
抵达贝尔库后,梅尔索和埃曼纽下了车。埃曼纽唱着歌,声音又大又走音。“你知道的,”他对梅尔索说,“是自然而然从胸口涌出来的。我高兴时会这样,去玩水时也会这样。”的确如此。埃曼纽总是一面游泳一面唱歌,歌声因水压而变得低沉,在海上是听不到的,但和他短而健壮的手臂动作节奏一致。他们取径里昂街。梅尔索昂首阔步。他身材高大,摆动着宽而厚实的肩膀。他跨步登上人行道的姿态,和优雅地扭腰避开挡住了他的人群的模样,可以使人感觉得出这个躯体特别年轻且有活力,能够带领它的主人体验最极致的肢体享受。休息时,他像刻意展现身体柔软度似的,全身只倚放于单侧臀部,像个透过运动已然明了自己身体风格的人一样。
他的双眼在略显突起的眉框下闪烁着,一面和埃曼纽聊着,圆滑而灵活的嘴唇噘了起来。他下意识地拉了拉领口,让脖子透透气。他们走进惯常去的餐馆。他们坐下来,默默用餐。晒不到太阳的室内凉爽许多。有苍蝇声、盘子碰撞声,以及交谈声。老板谢雷思特朝他们走过来。他身材高大,留着八字胡。他撩起围裙抓了抓肚子,再任围裙垂落。“还好吗?”埃曼纽问。“和老人一样。”他们寒暄闲聊。谢雷思特和埃曼纽交换了几声惊叹的词语,互相拍了拍肩膀。“其实老人呀,”谢雷思特说,“他们有点蠢。他们说五十岁的男人才是真正的男人,但这是因为他们自己五十几岁了。我呀,有个朋友,他只要能和儿子在一起就很快乐。他们一起出去玩,到处找乐子。他们也去赌场,我朋友说:‘干吗要我和一群老人出去?他们每天尽说自己吃了泻药,或说肝在痛。我还不如跟儿子出去。有时他去泡妞,我便假装没看见,自己去搭电车。再见,多谢了,我玩得很开心。’”埃曼纽笑了。“当然,”谢雷思特又说,“他不是什么显赫人物,但我挺喜欢他。”接着他又对梅尔索说:“我宁可这样,也不喜欢我以前的一个朋友那样。他成功了以后,跟我说话头总抬得老高,相当做作。现在他没那么傲气了,他什么都没了。”
“活该。”梅尔索说。
“咳,做人也别太苛刻了。他及时把握住好机会,那样是对的。他弄到了九十万法郎哪……唉!如果是我多好!”
“你会怎么做?”埃曼纽问。
“我会买一栋小木屋,在肚脐上涂一点胶水,再插一面旗子。这样我就能等着看风从哪边吹来。”
梅尔索安安静静地吃着。后来埃曼纽向老板聊起他在法国马恩省打过的那场战役。
“我们这些佐阿夫
[1]
[1]
佐阿夫(zouave),法国军队中的轻步兵,一八三一年于阿尔及利亚成军,成员原为阿尔及利亚人,后全改为法国人。
呀,被编入轻步兵营……”
“你烦死人了。”梅尔索冷淡地说。
“指挥官说:‘冲呀!’我们就走下去了,那里像壕沟,只有一些树。他们叫我们把枪上膛,但眼前一个人也没有。我们就这样往前一直走,一直走。忽然间一堆机关枪朝我们乱扫,所有人统统倒地,跌叠在一起。死伤的人好多好多,壕沟里血流成河,都能划小船了。有些人大喊:‘妈!’太凄惨了。”
梅尔索站起来,把餐巾打了个结。老板去厨房门后面记下他的餐点。门是老板的账本。有异议时,他就把门整片拆下来,把账目扛出来。老板的儿子贺奈,在角落吃着水煮蛋。“可怜的家伙,”埃曼纽说,“他的胸口有毛病。”的确如此。贺奈通常沉默又严肃。他并不太瘦,眼神很明亮。此时,一位客人正向他解释说肺结核“只要愿意花时间仔细治疗,是可以痊愈的” 。他频频点头,一面吃一面凝重地应着。梅尔索走到吧台坐在他旁边,点了杯咖啡。那客人继续说:“你认不认识尚·佩雷兹?就是瓦斯公司的那个。他死了。他只是肺有毛病,但他坚持出院回家。家里有老婆,而他当老婆是匹马。生病害他变成那样。你知道,他总是在他老婆身上。她不愿意,但他凶得很。结果每天都来个两三回,生病的人就这么没命了。”贺奈嘴里含着一块面包,不禁停止咀嚼,愣望着对方。“是呀,”他终于说,“坏事来得快,但去得慢。”梅尔索在满布雾气的大咖啡壶上用手指写着自己的名字。他眨了眨眼睛。从这个静默寡言的肺结核病人,到满腔歌声的埃曼纽,梅尔索的生活每天在咖啡味和柏油味之间来回摆荡,与他自身很疏离,他漠不关心,也远离了他陌生的心和真相。相同的事情,在其他情况下本该深深吸引他,现在他却不想再谈论,因为他正亲身体验着它们,直到他回到房间,用尽全身的力气和谨慎,去灭熄在自己内心燃烧的生命之火。
“梅尔索,你比较有素养,你倒是说说。”老板说。
“够了,改天再说。”梅尔索说。
“哟,今天早上是吃狮子了你。”
梅尔索微微一笑,从餐馆出来,过马路,上楼回到自己的房间。他的房间位于一家马肉铺楼上。从阳台向外探头,就能闻到血腥味,还能看到招牌上写着:“人类最高贵的战利。”他躺在床上,抽了根烟,随即入睡。
他待的这个房间,是昔日母亲的房间。他们在这个三房的小公寓已住了很久。只剩下他一人后,他便把另两个房间租给朋友介绍的一位制桶匠,制桶匠和他姐姐一起住;他自己则保留了最好的房间。他母亲死时五十六岁。她长得美,以为可以凭着美貌过上好日子、大放光彩。年约四十时,她得了一场重病。她无法再穿华服、施脂粉,只能穿病人服,脸庞因可怕的浮肿而变形,双腿水肿使她不便于行走,整个人毫无活力,最后变得半瞎,只能在毫无色泽、无力整顿的屋子里盲目摸索。最后一击既突然又短暂。她原本即有糖尿病,但她不以为意,满不在乎的生活方式又加重了病情。他不得不中断学业,工作赚钱。直到母亲死以前,他仍持续阅读和思考。十年期间,生病的母亲忍受着这种生活。这场折磨历时太久,周围的人都习惯了这场病,并忘了病情若太严重可能会致命。某天,她死了。附近的人很同情梅尔索。大家对葬礼很是期待,纷纷谈起这位儿子对母亲的深厚情感,也恳请远房亲戚切勿哭泣,以免徒增梅尔索的哀伤。大家请求他们要保护他,要多关心他。他呢,穿上自己最好的行头,手里拿着帽子,注视着一切筹备事宜。他跟随了送殡队伍,参与了宗教仪式,撒了那一撮土,也和许多人握了手。对于载送宾客的车辆这么少,他仅这一次感到意外并表达了不满。仅只一次而已。隔天,公寓的一扇窗户即出现一张告示:“出租”。如今,他住在母亲的房间。以前,尽管贫穷,有母亲伴随,自有一种温馨感。晚间,他们聚在一起,在煤油灯旁静静地吃东西,这种简约和静谧,有一种隐而不宣的幸福感。四周的巷弄安静无声。梅尔索望着母亲无奈的嘴,他笑了。她也笑了。他继续吃饭。灯有点冒烟。母亲以相同的疲惫手势调整灯,即仅伸长右手,身体往后仰。“你不饿了。”稍后她说。“不饿了。”他或抽烟或阅读。前者情形时,母亲会说:“又抽烟!”后者情形则说:“把灯拉近一点,不然眼睛要坏了。”如今,孤独一人的贫穷,却是一种悲惨的不幸。每当梅尔索哀伤地想起逝去的母亲,其实他是在可怜自己。他大可另找更舒适的住所,但他割舍不下这栋公寓和它贫穷的气味。在这里,至少他还能回到昔日的记忆,而在他刻意低调隐匿自己的人生中,这种沉重而漫长的对照,让他得以在悲伤和懊悔的时刻继续存活。他保留了门上的一块灰色纸板,纸板边缘已起毛,上面有母亲用蓝色铅笔写着的他的名字。他留下了那张铺着锦缎的老铜床,以及祖父的肖像。祖父留着短胡子,浅色的眼珠静静不动。壁炉上,有一座停摆的老时钟,周围环绕着男男女女的牧羊人摆饰,还有一盏他几乎从不点燃的煤油灯。略微凹陷的麦秆编椅、镜面泛黄的衣柜,和缺了一角的盥洗小桌
[1]
[1]
自来水尚未普及的年代,卧室里的盥洗小桌常配有大水壶和水盆,乃至镜子,供梳妆盥洗。
,这些令人退避的景象,对他而言不存在,因为习惯早已将一切磨蚀殆尽。他这样是漫步在一个影子般的公寓里,完全不需耗费力气。若换了别的房间,他势必要重新习惯,也必须挣扎一番。他想要尽量减少自己在世上的面积,并沉睡到一切耗尽为止。基于这个目的,这房间很适合他。它一侧面向马路,一侧面向一个总是晾满衣物的阳台,阳台再过去一些则是几片由高墙围着的狭小橘树果园。偶尔,夏天夜里,他让房间一片漆黑,并打开面向阳台和阴暗果园的那扇窗。随着夜愈来愈深,浓郁橘树的气味飘上来,如薄围巾般揽住他。整个夏夜,他的房间,乃至于他自己,都沉浸在既扑朔迷离又浓烈的芳香中,仿佛了无生气了好几天后,他首度打开自己的人生之窗。
他醒来时满嘴睡意,浑身大汗。时候很晚了。他梳了梳头发,冲下楼去,跳上电车。两点零五分时,他已在办公室内。他的工作场所是个大厅堂,四面墙壁共有四百一十四格柜架,均叠满了卷宗。这厅堂既不脏也不阴森,但终日让人感觉像个骨灰存放处,死去的时光在此腐化。梅尔索核对提领单、翻译英国船只的补给品清单,三点到四点之间接待欲寄送包裹的客人。当初应征的这个工作,他其实并不喜欢。但起先,他觉得这不失为一道通往人生的出口。这里有许多富有活力的脸孔,有熟人,有一条通道和一阵气息,让他终于感觉得到自己的心跳。他借此逃离了办公室组长朗格卢瓦先生和三位打字小姐的脸孔。其中一位打字小姐长得挺漂亮,不久前刚结婚。另一位与母亲同住。还有一位则是年长的赫碧雍女士,为人健朗又有骨气;梅尔索喜欢她华丽的辞藻,和她对于朗格卢瓦所谓的“她的不幸”的内敛态度。朗格卢瓦与赫碧雍女士曾数度交锋,每次总是她胜出。她瞧不起朗格卢瓦,因为汗水常使他的裤子紧贴着屁股,也因为他一见到主任就慌乱不已,有时在电话里一听到某位律师或状似名气响亮人物的名字,他也会紧张。这个可怜的家伙总努力亲近赫碧雍女士,或试着讨好她,但徒劳无功。这天晚上,他在办公室里晃来晃去。“赫碧雍女士,您也觉得我这个人不错吧?”梅尔索翻译着英文“蔬果,蔬果”,一面望着头上的灯泡和绿色纸板折成的灯罩。他面前有一份色彩鲜艳的日历,日历上的图是远洋渔民
[1]
[1]
远洋渔民(Terra-Neuvas),指十六至二十世纪间,每年自欧洲沿岸远赴加拿大捕猎鳕鱼的渔民。
的朝圣节
[2]
[2]
朝圣节(le pardon),法国不列颠地区的传统天主教庆典。
。濡指台、吸墨纸、墨水和标尺在他桌上一字排开。从他的窗户可看到由黄色和白色货轮自挪威运来的成堆大型木材。他竖起耳朵听。墙壁外面,人生在海上和港口无声而深沉地一次次呼吸,离他既遥远又贴近……六点的钟声释放了他。这天是星期六。
回到家里,他躺到床上,睡到晚餐时间。他煎了几个蛋,未装盘就直接从锅子里吃掉(没配面包,因为他忘了买),然后躺下来,立刻睡着,睡到隔天早上。他于快要午餐前醒来,梳洗完毕,下楼用餐。回来后,他填了两个字谜游戏,小心翼翼剪下一幅库鲁申食盐的广告,贴入一本已贴满了广告上那位下楼梯逗趣老爷爷图片的簿子里。完成这件事后,他洗了洗手,去阳台。下午天气很好。不过路面油腻肮脏,路人稀少且行色匆匆。他仔细凝视每个路人,直到那人出了视线范围,再找个新的路人继续凝视。最初是外出散步的一家人,两个小男孩穿着水手装,短裤到膝上,拘束的衣着令他们姿态僵硬;还有个小女孩打着粉红色大蝴蝶结,穿着黑色亮皮皮鞋;他们后方的母亲一身咖啡色丝质长裙,长得脑满肠肥;父亲手持拐杖,较为斯文。稍后经过的是住在这一带的几个年轻人,头发抹着发油,红色领带配上非常合身、有镶边小口袋的西装外套,脚上穿方楦头皮鞋。他们要去市中心的电影院,正赶着搭电车,嘻笑得非常大声。他们之后,街头逐渐空旷。各处的表演已经开始。现在这一带只剩看店的店主和猫了。街道沿线榕树上方的天空尽管晴朗,却无光泽。梅尔索对面的烟商,拉了张椅子到自家小铺门口,跨坐到椅子上,双手抵着椅背。刚才人满为患的电车,现在几乎空空荡荡。皮埃罗小咖啡馆里,服务生在无人的店内清扫着地上的尘屑。梅尔索学烟商那样,把椅子反过来坐,连抽了两根烟。他回到房间里,掰了一块巧克力,回到窗边吃。不久天色变暗,随即又拨云见日。但来了又走的云,仿佛在街头留下了必将下雨的承诺,使街上显得暗沉。五点时,电车在喧闹中抵达,从郊区的体育馆载回一群又一群站在踏板上和倚着栏杆的足球观众。之后的电车则是载回球员,由他们所提的小箱子即可轻易辨认。他们大声地又喊又唱,说他们的队伍不会完蛋。好几个人向梅尔索打招呼。其中一人高喊:“我们痛宰了他们!”梅尔索只摇了摇头说:“是呀。”车辆愈来愈多。有些车在挡泥板和保险杆上插满了花。接着,这一天又迈进了一些。屋顶上方的天空染上一层红。暮色降临之际,街上又热闹起来。散步的人回来了。累了的孩子,有的哭闹,有的由大人牵着走。此时,附近电影院散场的观众如潮水般涌入街上。梅尔索看到,年轻人出来时果决而夸大的手势,无异如旁白般暗示着他们看了一部冒险片。从市区戏院回来的人则较晚才到。他们神情比较严肃,笑声和喧闹之间,在眼神中和姿态上,仿佛又浮现出对电影里看到的光鲜亮丽生活的怀念。他们流连街头,来来往往。梅尔索对面的人行道上,最后形成了两股人潮。未戴帽子而互揽着彼此手臂的妙龄女子,构成了其中一股人潮
用户评价
叙事学是文学研究中的热门领域,而本成果所开展的“空间叙事研究”则是此领域中新的理论方向,是目前叙事学研究中最有发展前景、最具学术潜力的领域之一。其研究目的,是对传统叙事学重视不够甚至严重忽视的叙事的空间维度或叙事作品的空间元素进行系统考察,进而对叙事与空间所涉及的问题展开了全面、系统的论述,从一个新的视角对叙事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属于文艺基础理论的创新研究,对于叙事学本身的学科建设,对于文学乃至其他学科的理论创新和研究方法的革新,都具有较为重大的价值。龙迪勇,江西宜春人,1972年出生,近年来所从事的空间叙事研究,拓展了叙事学研究的领域,是国内最早提出建构“空间叙事学”的学者。
评分没什么感受,写的又发表不了。真是坑
评分东西很好,内容也不错哦
评分3.全书用100个专题叙述了从中国境内的人类起源到晚清的中国历史,脱离了一般历史书编年体或章节体的窠臼。
评分不错的 很便宜
评分思嘉眼中希礼有一道神秘的光圈围绕着,为此思嘉必须得到他。思嘉的厌恶分明,立场坚定,只要让她明白了或者要做的事,她可以不择手段的去争取,作者在向我们毫无保留的展现她的贪婪、自私、虚荣.以及她的暴躁与率真,我认为我们没有必要去对她的这些与生俱来的本性说三道四,让人觉得可悲的是思嘉一直以来所追求的仅仅是光环是梦幻。当思嘉认清他时,认清她一直以来所追求的仅仅是虚幻是光环时,她却失去了瑞德的爱!可惜的还是思嘉,因为她的简单率真,为此付出了她此生最高昂的代价!
评分加缪的处女作,必须要看
评分5.本书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2015年度基础研究重大成果”,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于2015年12月25日播出。
评分这四本书印刷精美,包装设计不错,很喜欢,谢谢!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5 book.qciss.net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大百科 版权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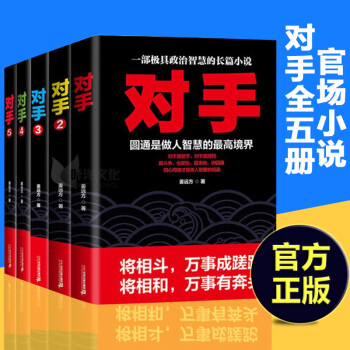






![根西岛文学与土豆皮馅饼俱乐部(2013年版) [THE GUERNSEY LITERARY AND POTATO PEEL PIE SOCIETY]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qciss.net/11360709/rBEhVVKO434IAAAAAAVcxxjGR1MAAF8RwNllKQABVzf349.jpg)





